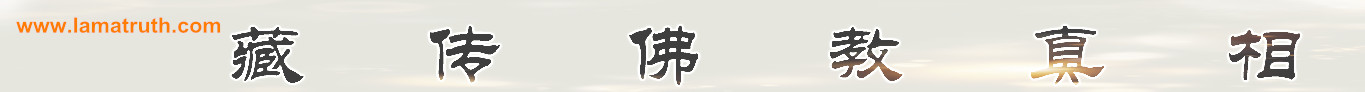| 首页 » |
【口袋书】 - 广论之平议〈二〉—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平议(连载四) |
第六目 智慧与方便 阿底峡《菩提道灯论》说: 离慧度瑜伽,不能尽诸障。为无余彻底断除,烦恼所知障, 故应具方便,修慧度瑜伽。般若离方便,方便离般若, 俱说为系缚,故二不应离。何慧何方便,为除诸疑故, 当明诸方便,与般若差别。除般若度外,施波罗蜜等, 一切善资粮,佛说为方便。 苦修方便力,自善修般若,彼速证菩提,非单修无我, 遍达蕴界处,皆悉无有生,了知自性空,说名为般若。 有则生非理,无亦如空花,俱则犯俱过,故俱亦不生。 诸法不自生,亦非他及共,亦非无因生,故无体自性。 又一切诸法,用一异观察,自性不可得,定知无自性。 七十空性理,及本中论等,亦成立诸法,自性之空性。 因恐文太繁,故此不广说,仅就已成宗,为修故而说。 故无于诸法,自性不可得,所有修无我,即是修般若。 以慧观诸法,都不见自性,亦了彼慧性,无分别修彼。 (《菩提道次第广论》附录) 阿底峡所说的前三偈,要断烦恼、所知二障,必须具方便与智慧,在六度中除慧度外,余五度皆为方便,当在本书稍后〈上士道章〉再说。阿底峡为了成立诸法不生的理论而说: 遍达蕴界处,皆悉无有生,了知自性空,说名为般若。 有则生非理,无亦如空花,俱则犯俱过,故俱亦不生。 阿底峡认为蕴处界诸法皆悉无有生,他从四个方面来观察:诸法有生、诸法无生、诸法亦有生亦无生、诸法非有生非无生;阿底峡把上四句全破了,说有生非理,无生如空花,亦有生亦无生也不对,非有生非无生全都无有生。所以阿底峡认定蕴处界诸法皆悉无自性生,无自性生即是无生。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空,阿底峡说一切法空就是空性、是智慧。这是因为阿底峡未证空性实相心,所以才误解空性之理,而成为无因论,成为恶取空、断灭空之人。 其实蕴处界诸法一定要依空性心阿赖耶识而说有或说无。实相心阿赖耶识是蕴处界诸法生成之因,阿赖耶识也是蕴处界诸法说为无生之因──将有生之蕴处界摄归无生之阿赖耶识心体中,则蕴处界诸法是阿赖耶识心体中的一部分,故蕴处界诸法亦是无生。若蕴处界诸法不摄归阿赖耶识心体,而是单依蕴处界自体来说,则是有生有灭之法。而阿赖耶识真实有,内含无量无数的业种及有漏有为法种、无漏有为法种等,透过业种及各类法种等之种子不断的现行运作,而有蕴处界诸法之生出,所以从阿赖耶识所含藏之种子运作,或从蕴处界自身来看,蕴等诸法则是有生。再从阿赖耶识如来藏自体的立场来看,蕴处界诸法是阿赖耶识如来藏所生,是阿赖耶识之一部分,与阿赖耶识不一不异,而阿赖耶识从无始以来即无生,故蕴处界诸法亦说为无生,所以大乘经中依此而说一切法无生。因此依于阿赖耶识而说蕴处界诸法非有生亦非无生,如此才是中道观。但阿底峡是中观应成派六识论者,不知蕴等诸法之所依的阿赖耶识,也不相信有阿赖耶识心体如来藏存在,读了大乘经所说的一切法无生语句以后,单单从蕴处界等一切法的生灭性,以自意所思所想来说一切法自性空,其实是虚妄想、是恶取空、是断灭空,落入增益执中,不是有智慧的人所说也。 阿底峡说: 法不从自生,非从他及共,非从无因故,由体无自性。又以一及多,观察一切法,其体不可得,固定无自性。……,为修故精说。 阿底峡这几句偈颂是以缘起性空之理,破外道的自在天创造一切法,及内道有宗,而自己却也陷入外道法之中,成为无因论、断灭论,他自己却不知道。阿底峡说:一切法非自生、非他生、非自他共生、非无因生,此四生都是无自性,所以诸法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生即是无生,也就是说没有此四种生的意思。因此阿底峡只认定诸法是无自性生,不必有根本因,单靠种种缘就能出生,是如幻如化的无因有缘而生;所以一切法无单独自性,是种种缘的和合生;一法或多法都是一样,都没有自体可得,故无自性。这就是从月称、寂天传下来的中观应成派“缘起有、自性空”的理论。 在圣 龙树菩萨的《中论》卷一中有提到: 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 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 但是圣 龙树菩萨此两偈颂之前提,已说明“八不”的主体空性心如来藏,依空性心如来藏所生出来的诸法与如来藏不一不异,所以说: 一、不自生:诸法不能由自己出生自己,否则诸法都应一分为二,诸法中的每一法都应同样有二体,一为能生之法,二为被生之法;或应诸法都能自生,则儿应自生,不应从母亲生,此已说明诸法都同样来自同一个本源如来藏。 二、不从他生:诸法固然不从自生,但亦不从他生,都应从自己所依附的如来藏心体中出生;否则自己的识阴六识等法在今夜眠熟暂灭以后,明日应可以从其他有情的如来藏中出生而成为另一个色阴所有的六识心,则天下大乱矣,然而天下不曾如是大乱,故知诸法必定从自己所附属的如来藏心体中出生,绝不从他而生。 三、不共生:自己的诸法一定是从自己的如来藏中出生,不必与他人的如来藏合作才出生自己的识阴六识,故说诸法不是自他共生,这也表示自己所有的诸法只会从自己的如来藏中出生,故亦不是由众多如来藏中共同所生。 四、不无因生:诸法之出生固然必须有种种缘,但是还得要有因,不是单单凭藉众缘就能出生而不必有因;是说诸法藉缘而出生时必定另有其因,此因即是有自体性及其他种种自性的如来藏心体,诸法是以如来藏为因而藉缘生出的,所以圣 龙树菩萨说“不无因”。 五、是故知无生:诸法由如来藏为因所生,诸法摄归如来藏而与如来藏不一不异,而如来藏从无始以来本自无生,所以诸法也是无生。 六、诸法自性不在缘中:诸法都是有生之法,故无自体性,有自体性之法只有如来藏;以现象界来看,诸法似乎都有自性,但诸法都不能无因唯缘而自己存在,故说无自性;必须是依如来藏所显示出来的无生体性,诸法才能有自性可说,所以说诸法的存在及运作时的自性并不在众缘中,是在如来藏中,若无如来藏的常恒及种种自性的支援,诸法即使仍有众生,也无法存在,故说诸法“不在于缘中”。 七、诸法无自性亦无他性:既然诸法的自性不在自体,也不在他缘,而是在如来藏中,故说诸法无自性;既然诸法都无自性,就表示诸法亦无他性,故也不可能眠熟断灭之后又自行出生。因此诸法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诸法无自性,也无他性,是依如来藏识为因,众缘和合而起,后时也由如来藏为因,由众缘的离散而坏灭,故虚妄不实。此圣 龙树菩萨有名的四句: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说必须有如来藏识为因,才能全部符合,否则就必须如应成派中观一样曲解 龙树的《中论》偈。因阿底峡否定第八识如来藏,在他未证空性心如来藏识的情况下,任他如何想像也是想不出来的,正是因为不知 龙树的《中论》偈说的都是真实如来藏的法性故。(此四句不生,将在第八章第三节第五目中再申论之。) 圣 龙树菩萨又接着写了一偈: 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中论卷第一》) 此四缘正好破斥应成派中观无因论的缘起性空理论。蕴处界万法是依父母及四大为缘而幻生幻灭,然须依“因”空性心如来藏;由如来藏为因,藉着无明……等众缘,方能有此蕴处界万法之缘起缘灭;若离空性心如来藏因,尚不能生起蕴处界,何况能有蕴处界所生万法?因此圣 龙树菩萨四缘当中,首句就道出第一个缘 ──因缘。所谓因缘就是如来藏心体以及如来藏内所含藏的七识法种及能生诸果的业种,这些法种及业种等皆依如来藏而有,由于有这些法种及业种等不断的运作,才能有一切法从如来藏心体中生出,否则即无蕴处界等一切法。换句话说,没有如来藏则没有一切法,因此如来藏即是一切法之总因。同样的,其他的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亦皆以如来藏为所依而有,这个道理将在本书〈毗钵舍那章〉中再论之。所以中观应成派所说不依如来藏为因,而说一切法单凭众缘就能生起的缘起性空说,是无因论、恶取空、断灭空,理由在此。 阿底峡又说: 故所有诸法,自性不可得;凡修习无我,即是修真性。 无因论者的修习无我,必定无法断尽我执的,因为必定恐惧落入断灭空中故。假使真的不恐惧落入断灭空中,能断尽我执而灭尽蕴处界全部,成为无余涅盘以后,也已成为断灭空,哪来真性可言?既无真性实存,哪来智慧可得呢?而且真性若是无我,但真性却本是不生的,是本然清净圆满的,根本不须如阿底峡所说要 “修习无我”才能成就,然而阿底峡的“真性”却是要修成的;纵使他真的修成了真性,却是灭尽蕴处界我以后的真性,则这个真性仍然是有生之法,有生之“真性”却是灭尽蕴处界后的空无、断灭空,怎能说是真性?纵使真的有真性存在不灭,将来当然不免缘灭而成为空无,因为是修而后有的缘故。故说阿底峡不是实证真性、空性心的人。 第七目 修无分别 阿底峡《菩提道灯论》说: 三有分别生,分别为体性,故断诸分别,是最胜涅盘。如世尊说云:分别大无明,能堕生死海;住无分别定,无分别如空。入无分别陀罗尼亦云:佛子于此法,若思无分别,越分别险阻,渐得无分别。由圣教正理,定解一切法,无生无自性,当修无分别。(《菩提道次第广论》附录) 什么是分别?阿底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分别的道理有深有浅、次第差异很大,前五识对五尘的分别,第六意识对法尘的分别,第七末那识对意识及法尘的分别,第八阿赖耶识对末那识心行的分别,以及对身根、业种、寿算、山河大地、四大的分别,差别万端,并非阿底峡所能知道。而阿底峡说不生三有,要断诸分别,其实是要断除诸分别之识,不是如同阿底峡所说的保留六识而断除语言分别;若阿底峡改说为断尽诸分别的六识,则从定性二乘人来说是正确的,前六识愿意永远自我断灭以后,意根就会接受而在舍寿时一同灭尽;七识全断,舍寿时即入无余依涅盘,从此就不会再有分别。但是不生三有,是二乘人的目的,阿底峡既然自认为不是二乘人,即不该认同二乘人灰身泯智的行为;而且二乘人所断的我见与我执,都不是阿底峡所能做到的,因为他既要维持双身法的四喜大乐,当然不能断我见与我执,否则双身法就无法继续再修了;可是阿底峡一生都没有放弃双身法的修持,所以他是连我见都断不了的,不该再高攀二乘人的实证。对大乘菩萨来说,一定要 “分别、生三有”,大乘法的持戒、入定、修慧,最终实证一切种智、四智圆明,历经三大阿僧只劫中,世世都必须要在三有中受生,也都必须要有分别心继续存在来分别法义的正邪,分别法义的是否实证圆满,才能成佛;故大乘人必须有分别心世世存在才能证道,诸佛、菩萨说法,乃至诸佛利乐一切众生永无穷尽,都必须以分别心行之,是故分别心绝对不能断除,是故必须世世受生而生三有。由于有分别才有世俗智慧之产生,有世俗智慧的众生才能学佛,学佛以后实证般若乃至一切种智,也都要有分别心继续存在,故能分别的自性并不是阿底峡所说的大无明,反而是智慧能出生与保持的原由。但阿底峡与寂天、月称、佛护等人一样,同以意识觉知心一念不生、不起分别作为悟境,作为般若的实证,认为心中起分别时就是大无明,这是严重误会大乘佛法无分别的真义。 第八阿赖耶识本来就住无分别定中,此无分别定才是真正的无分别;此无分别定,从来不分别六尘中的一切法,而且这无分别定的境界相,不是修行以后才得,而是一切众生各自的第八识如来藏本来就已经有此无分别定;证得第八识的无分别大定,才能使意识觉知心拥有般若大智慧。 又意识心入定,还是有分别,因为意识心本来的体性就是时时对六尘中的一切境界起分别,除非是在眠熟等五位中暂时断灭而不生起。所谓意识心入定,于境界不起攀缘,不起贪等烦恼,才称为意识心入定;但是入定以后仍然能对定境中的内容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即是已经分别定境中的六尘或法尘境界了,故定中仍然是有分别。如果意识心入定后就完全不起分别,那就是痴呆相,对于修定、修慧都是一无是处。 《楞伽经》卷四说: 复次,大慧!自心现妄想,八种分别:谓识藏、意、意识,及五识身。 所谓“识”即是分别的意思,经说“识藏”即是空性心如来藏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而与七识俱,此空性心如来藏在三界内运作时,有其远离六尘见闻觉知的分别性,既能了知意根及意识心的心行,能了知妄心意根的作意,也能了知身根四大种的变化,也能了知业种异熟果报的次第……等,能作如是等种种六尘以外的种种分别。 又《金刚三昧经》卷二说: 无分别中能广分别。 此中无分别及广分别的心,都是指空性心如来藏,如来藏能作六尘以外的种种分别,因此说如来藏无分别心能作广分别;而祂的广分别,并不是凡愚七识心所能知道的;菩萨证悟后,悟后起修,发起道种智以后,才能对如来藏的广分别有一些较深入的了解,这是究竟佛地才能全部了知的智慧。 为什么又说空性心如来藏是无分别呢?《金刚三昧经》卷二又说: 菩提性中无得无失、无觉无知、无分别相,无分别中即清净性。 这是说空性心如来藏本体,本来自性清净无染,从来都离六尘中的见闻觉知,故从来不分别苦乐、美丑、长短、方圆、人我、生死、染净……等。因此众生不论有没有开悟,如来藏这个无别心是与能广分别的自性,无时无刻都同时显现着,无时无刻和合运作而没有间断,除非眠熟或闷绝……等五位中。只是众生开悟前被烦恼所障碍,不知道此无分别心在什么地方,才会因愚痴无明而认为有分别的觉知心是真我,因此而轮转生死;阿底峡就是这样的人,他说: 佛子于此法,若思无分别,越分别险阻,渐得无分别。 他的意思是说:学佛的人只有六识“有分别心”,没有第八识“无分别心”,要透过“佛法”的修习而把六识“分别心”转变为白痴一般的“无分别心”。这是因为阿底峡没有证得空性心,不知道六识“分别心”与第八识“无分别心”都是同时存在、同时显现、同时运作的道理,才会妄想把有分别的觉知心修行转变成无分别的白痴心。但是他的想法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分别心是永远都会有分别的,不可能修成永远都无分别的真心;而无分别心如来藏是本来就无分别的,不必他去修行而把有分别的自己转变成无分别。不论众生有没有学佛,都同样是有分别的意识与无分别的如来藏同时存在及共同配合运作的,这是中观应成派的阿底峡所不知道的,但是宗喀巴却援引阿底峡的论着来为自己的六识论撑腰,并非有智之人。 《楞伽经》所说的“意”是指意根,又称第七末那识。末那识只对意识作分别,并对法尘只作少许分别,祂的分别慧功能不很好。譬如眠熟无梦时,意识断灭了,忽然有打板的声音在法尘中出现了,末那识警觉法尘有重大变动,自己却无法了知那是什么,于是就作意而使如来藏流注意识种子,生起意识来作详细的分别,才会知道是打板的声音,才知道应该起床了。或如在定中,末那识时时注意法尘的动静,法尘一有大变动,马上就使意识出定,以便分别是什么大变动、该不该回应。如是菩萨对末那识的分别心,也是不该断除的;如果断了末那识的分别性,即会使得末那断灭了,则入无余依涅盘,一切法就都不存在了。若方便说所谓的末那识入定,是说末那识决定接受意识心的觉观分析,使得意识依附心一境性中安住,暂时不受六尘所影响,看似末那也入定而不攀缘,但实际上末那是不与定相应的,仍然是在遍缘一切法的。又意识于境界不攀缘,也要取决于末那识对六尘执着的减少;如果末那识对六尘的执着不能减少或修除,必定会继续攀缘外境,因此意识也不能入定。假使末那识的俱生我见、俱生我执不能修除,意识心也是无法证得灭尽定的;但是这些都要靠意识心如理作意的配合共同运作来修除愚痴无明、修除执着以后,才能做得到。所以修定者,不是要把意识分别性修除而变成无分别心,如果是这样修定的人,则他一定是痴痴呆呆的人,既不能知道如何入定、出定,也不会知道自己在定中定外做了什么事,所以修定并不是如阿底峡所说的方法;而无分别定是第八识本来就有的法界大定,不需要像阿底峡一样把意识来住入无分别的痴呆状态中。若是想要证无分别定,是要参禅寻觅从来无分别的阿赖耶识心体所在,自然就能证得无分别定而成就无分别智,则应该有分别心意识继续修行而寻觅无分别性的第八识心,这才是真正的大乘成佛之道。欲修成佛之道者,则意识的分别心不应如二乘人一般的灰身泯智,二乘人得要把意识、末那断除才能成办入涅盘,违背大乘成佛之道的行门。但是意识心的种种行为,都要靠末那识的支持及配合运作,才能存在及运作;而末那识一定要继续保持不断,才能世世受生、继续学佛,直到三大阿僧只劫以后成就佛道,所以末那识的少分分别性及少分的法执,在成佛以前是不该如二乘圣人般的修除灭尽。 第八目 道位次第 阿底峡《菩提道灯论》说: 如是修真性,渐得暖等已,当得极喜等,佛菩提非遥。(《菩提道次第广论》附录) 如上已知藏传佛教密宗应成派中观的所谓“空性”,即是一切法空,这其实不能说为“空性”,应当说为“空相”。“空相”者是说有相法的五蕴空、十八界空,一切法空,即是《心经》所说的“是诸法空相”。而“空性心”只有一法,只指如来藏本识而言。而藏传佛教密宗否定如来藏之法,却说想要证得真正的空性心,那是缘木求鱼。 又阿底峡说: 如是修真性,渐得暖等已,当得极喜等。 以其未证悟实相的身分来说,他这是颠倒说。煖等四加行位的证得只是六住位菩萨,只能说是顺解脱分与顺决择分圆满,此时只能说已经具备了证空性心的条件而已,必须再依善知识临门一脚帮助,才触证空性心如来藏。证空性心后,还要历经十住、十行、十回向位圆满才能登见道圆满位之极喜地。入地后还要地地增上,至十地、等觉位、妙觉位圆满,才说圆满佛菩提。所以从菩萨证空性心开始计算到成佛,还要约二又三分之一阿僧只劫的时间待超度。又阿底峡所说的修真性,是暗喻双身修法中的六识知觉性;“渐得暖等已”,是说拙火已经开始生起,生起次第即将圆满时;“当得极喜等”,是暗喻即将获得双身法中的淫乐喜悦,“等”字是暗喻初喜乃至全身遍乐的第四喜。然而佛菩提之路是很遥远的,不是藏传佛教密宗以外道双身法的意识境界所能到达的,也不是藏传佛教密宗以双身法的身乐觉受可以成佛的,故即“身”成佛的说法是荒诞不经的,因为成佛是在心而不在身;假使以双身法的乐空双运意识境界,再努力进修无量无数的阿僧只劫以后,仍然只是意识境界的身乐觉受,从来不能涉及实相境界,不能涉及实相心的心境界,永远都进不了三贤位中,何况入地?更别说是成佛了! 圣 弥勒菩萨《现观庄严论》论中,曾提到加行四法──即“煖法、顶法、忍法及世第一法”。四加行在佛法修学次第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未证空性心-未开悟明心-之前,学人必须先成就此四法,否则无法趣入佛法大门,不可能成为三贤位中的第七住位菩萨。藏传佛教密宗上师、仁波切、格西、喇嘛、“法王”等人,任意解释此四法,以自设的四种加行法来取代真正的四加行,都违背圣 弥勒菩萨论中所说正理,都不可能获得煖等四位成就。譬如《密勒日巴全集》中,密勒日巴解释说: 所谓四加行:十万大礼拜、十万上师咒、十万金刚萨埵百字咒以忏悔、十万供养曼陀罗或曼达。(百字明咒的意义也是双身法) 白教上师陈健民说: 四加行的内容,一个就是归依、一个就是礼拜、一个就是百字明、一个就是供曼达。 又《大乐光明金刚乘大手印》所说的四加行: 一.归依、发菩提心,从此成为佛子、大乘行者。 二.供曼达,这是累积福德资粮的方法。 三.观想金刚萨埵及念诵百字明,这是清净业障的方法。 四.上师相应法,这是获得上师加持的方法。 宗喀巴《归依发心仪观行述记》中说四加行: 一.归依发心,二.金刚萨埵百字明或三十五佛忏,三.供曼陀罗,四.上师瑜伽。 上师瑜伽则是每天观想上师与自己交合,或是观想上师与明妃在自己头顶上的虚空中交合,所出不净物从自己头顶灌入中脉顶轮,然后下降至海底轮引生淫根的乐受。 以上所举藏传佛教密宗的四加行,都是以佛法的名相为外表,骨子里都围绕在双身修法上转,正是假名佛法的外道。真正佛法的四加行,是修学者开悟破参前最重要的知见与修行方式,因为修习四加行圆满后,因缘成熟一念相应明心证真,学者就可以证入真见道“唯识性”中,进而悟后复能现观修证相见道而了知“唯识相”中的种种法的相貌,因而证解确实有阿赖耶识的存在,因现观而知道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所生,了知万法唯识的真义。“万法唯识”,就是讲阿赖耶识能生显一切万法的意思,也就是说三界一切万法都是由真心如来藏阿赖耶识所生所显;但是密宗古今上师都不实修亲证阿赖耶识,往往以观想中脉内的明点取代阿赖耶识心体,应成派中观更是极力否定阿赖耶识的真实存在,当然不可能实证阿赖耶识实相心,更不可能现观一切法都是八识心王和合运作而从阿赖耶识心中出生,就不可能了知万法唯识所述的真实义理,所以他们都是唯识学的门外汉,却空言懂得唯识学、却极力贬抑唯识学;若是真懂唯识学的人,都是双具虚妄唯识的七转识内容及真实唯识的第八识内容,都能现观七转识的虚妄,也都能现观第八识的真实与如如性,怎会否定第八识?又怎会以观想所生的明点来取代第八识?故说密宗都是不懂唯识学的凡夫外道。 四加行有四个层次:煖位、顶位、忍位、世第一法,四位修习圆满就可证得“所取空”及“能取空”,我见已断除了,已经成就声闻初果的见地,成为声闻解脱道中的初果圣人了,这也是具足了大乘见道资粮,待一念相应时即能亲证法界实相阿赖耶识如来藏,就可得入第七住的不退转住菩萨真见道位;如是亲证实相的见地,三乘菩提中的疑见全部断已,以后纵使有大名声恶知识笼罩或劝说,也都不会再退转此种见地。 要修习四加行成就而无碍于参禅的进展,必须具备五个条件: 一、护法勇猛心,护持正法无所畏惧。 二、舍心,在正法团体布施、护持不断。 三、功夫,有动中的基本定力。 四、正知见,有正确的禅法知见。 五、无慢,渐除障道慢心等性障。 以上五个条件得要在日常生活的身口意行中不断的熏习,使心与解脱相应,熏习圆满时称之为“顺解脱分”。然后继续加功用行,就能证得“所取空”及“能取空”,此是为“大乘真见道明心证真”作准备,这阶段的过程就是明心前的四加行。 四加行又称为四善根,随顺正法的熏习,趣近见道的成就,在疑惑中得决定心,具足正知正见、具足择法眼,能决择诸方善知识是否已断我见,能决择彼等所说法义是否能使人确实断除我见,所以四加行又称“顺决择分”。四加行的修习,必须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相空中起“四寻思”,即思惟“名、名义、名义自性、名义自性差别”;四寻思若能观行彻底,则得“四如实智”,确实断除我见,亲证声闻初果或大乘通教初果。 四加行的观行,可分四个阶段作观行。 一、创观:就是首次观察之意。是观照到能取的七转识,以及所取的名、义、自性、差别,都是所生法,虚妄不实;并经由闻法而知悉五蕴之名、义、自性、差别,都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也都是人为施设的假名。如是观行,就会发起般若的闻慧与思慧,对如来藏真实的体性,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虚妄,有初步的了解,因这样的现前观察,依“明得定”而发“下寻思”,现观所取六尘皆是所生法,无常空,非真实有,思慧生起了,与大乘见道有一分相近了;如同钻木取火时,烟尚未起时已有热煖之相,称为“煖相”。 二、重观:就是再次深入观察的意思,对末那的遍计所执性设法了解,对于所执取六尘境界的名、义、自性、差别深入思惟所取的六尘境界都是缘起性空,体会到一念不生之灵明觉知心是假的,是意识心,是缘生法,依“明增定”而发“上寻思”,如是再次深入现观“所取一切法空”,如此观察四寻思到达顶点,是世人所能了知的最究竟观察,称之为“顶相”。 三、经过创观及重观,就会依“印顺定”发起“下如实智”,有下如实智就有“顺决择分”,印证决定能观的五蕴不是真实有,随顺于此而不动摇,已经确认能取的六识心都是所生法,都是无常空,故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诸法中,并无一法是真实常住的我;但是尚未找到真心故,所以无法印持能取心七转识确实是空,故于此能取空的观行只能成为顺乐忍,是为“忍相”。 四、证印顺忍后,再深入观察能取的六识心与所取的六尘境界的自性差别,深入确认能取与所取皆是无常故空;譬如睡眠无梦时,六识断灭,对五尘境及法尘境不知不觉,因而印证能取的六识是虚妄不实,因此能取的六识是空;再深入观察所取的六尘境界,证实六尘确实要依五色根、意根、外六入才能出生与存在,深入观察,无所不至而了了能知所取一切境界皆空而不实。由此观察前六识、六尘都没有常恒不灭的自性,因此从日常生活中就可证知觉知心的意识不能到未来世,因而证得能取与所取皆空。 之后再作更深入的观察,六识的生起有三个条件:有生灭的五色根、六尘、末那识,其中若有一条件不具足,六识就不能生起;譬如眼根坏了眼识就不能生起,其他五识也是一样。因此六识的生起是依他起,有依他性就会依他灭,不是自在性。又五根对五尘而生法尘,意根对法尘而生意识,意识对法尘详细了别之后,而使意根生起遍计所执性,也就是我执,因此意根的我执也是间接依他起,非自在性。因此,在忍位中对所取空已了知接受,接着就印证受、想、行、识都是无常性,于此位中,心心无间而不曾怀疑自己所观察之“能所取俱空”,如此依“无间定”发起“上如实智”,就能双双印证所取能取都是空,而成就世间凡夫异生位第一无上之法,故名“世第一法”,我见确实已经断除了,三缚结已不再存在了。以上四阶段观行圆满,已证初果而不会再落入蕴处界我之中,已近真见道的缘故就可以修学大乘禅宗的法门,参禅求证法界实相,直到因缘成熟时一念相应而破参开悟的时节到来;一旦破参而确定不移了,就成为不退转的七住菩萨,入大乘真见道位。 阿底峡说:得“煖”等已,可证得初地等,这是错误的说法。依据《成唯识论》的开示,证得能取与所取二空后,还在六住满心位,尚须明心悟真,成为第七住菩萨;然后眼见佛性,成就世界身心如幻的现观,则圆满第十住位;再历经亲证实修十行、十回向位应有的功德与现观,如是三十心圆满才能登地。然后从初地入地心开始,地地增上十地无生法忍智,如此地地增上,历经二大阿僧只劫才能成佛。因此佛菩提的路,于一般凡夫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如果按照佛菩提道次第渐修,复有真正的善知识指导,而不是依止假名善知识,不走错路、歧路、回路,依大善知识所开示戒慧直往超劫精进的别教法道,还是可以快速到达佛位;若依藏传佛教密宗的修法而不舍,始终都在色身的乐触上用功而说即“身”成佛,唯有下堕三涂的机会,连欲界都超脱不了,更谈不上证解脱、证实相,来世也将失去人身,无数阿僧只劫以后仍然不能成佛。 阿底峡说:“如是修真性,渐得煖等已,当得极喜等,佛菩提非遥。”如果按照密宗的道位次第与行门来说,佛菩提果是绝对无法到达的。如何说呢?当菩萨明心悟真之后,悟后发起般若实相智慧,进修般若别相智圆满,复修学亲证诸地无生法忍而直到佛地,必定要修学唯识道种智,唯识道种智才是真正的增上慧学,道种智圆满时名为一切种智,证得一切种智了才算是圆满佛地的一切智智。而藏传佛教密宗诸师,否定三转法轮的唯识诸经,说唯识诸经是不了义,妄说是钝根人所学,譬如宗喀巴《密宗道次第广论》第八页如是说: 此诸补特伽罗之道,即是趣向一切种智之大乘也。波罗蜜多大乘,其道总体唯有尔许。此就见解分别有二,谓中观师及唯识师。然彼二师非可说其乘有不同,故乘唯一。由于实义有尽未尽,故知前是利根,后是钝根。此般若波罗蜜多乘,正为中观师宣说;其唯识师,为彼所兼摄庸常之机耳。 由此可知藏传佛教宗喀巴等人根本不懂大乘法义内涵与道次第,也误会中观与唯识分位差别的正义,由于藏传佛教历代诸师(觉囊派部分祖师除外)无法实证中观与唯识,宗喀巴承袭邪见且自己错解、生慢,对于唯识师不屑一顾,瞧不起唯识师,说之为钝根;他说大乘成佛的根据是一切种智,又说波罗蜜多大乘的修学目的 ──道的总体也是唯有一切种智;但是他不知道中观修学到最彻底时只是般若的总相智与别相智,无法成就一切种智,当然不能成佛;更何况连真实的中观都无法亲证的宗喀巴,否定了本识如来藏以后绝无可能亲证如来藏而发起中道观行的境界,如此胡言乱语,如何能知中观圆满后所应修的唯识种智妙法;他也不知唯识师所修的唯识正理,乃是中观成就以后才能实修的一切种智,他不知唯识师所修证的正是成佛所凭藉的一切种智;诸地菩萨都是纯依一切种智而修,修的都是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的智慧,就是无生法忍的智慧,名为道种智;道种智修学圆满了,就是佛地的一切种智;种智之学唯有利根者乃能亲证之,此非凡夫异生与愚昧的二乘圣者所知,乃至亦非大乘别教中初悟浅悟者所能知,然而此等修学种智而智慧深妙的诸地菩萨,在藏传佛教凡夫外道宗喀巴的眼中却是钝根者,真是颠倒至极的世间狂妄异生也。 宗喀巴将一切种智所依的如来藏否定了,就永远都无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可修证了,当然无法成佛,但他却仍想成就佛地的一切种智。而且宗喀巴所宗的应成派中观,又是无因论一切法空的断灭空,灭尽蕴处界以后已成为断灭空,然后又恐惧堕入断灭空中,再度执取五蕴为真实不坏之常住法,建立双身法第四喜乐触的即“身”成佛外道妄想理论,故是兼具断见与常见的外道邪见,是远离般若波罗蜜多大乘道,因此永远也无法证悟空性心,故无法观察唯识性,无法进入大乘见道位中,无法亲证中道观行的真实理;因此,宗法“藏传佛教应成派中观”的宗喀巴,对中观实无所证,对唯识学亦因严重误会而毫无所知,更何况对成佛之道的内涵与次第能够了解?因此之故,他只好瞎编淫秽不堪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来替代唯识增上慧学,专在色身相应的淫根乐触上广作文章。宗喀巴当然知道“应成中观”这个过失必坠入无因论的断灭见中,只好回头建立意识心,说是常住的,以免落入佛所诃责之外道断灭空中;这样一来,其违佛所说,高举本质为印度教性力派的外道见,妄说为“秘密金刚乘”,以之高推为更胜于大乘者,如此建立意识的常住说,才可以使藏传佛教密宗双身修法乐空双运的乐触境界得以成立,因为乐空双运不但是色身境界,也是意识的境界,所以宗喀巴仍然对乐空双运极为爱乐,认为是究竟法,妄说是修成报身佛的究竟法,其实都是我见等一念无明及无始无明妄想。(待续) |
|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