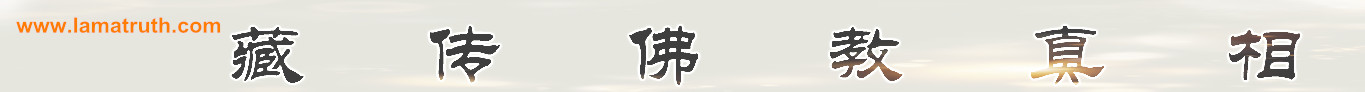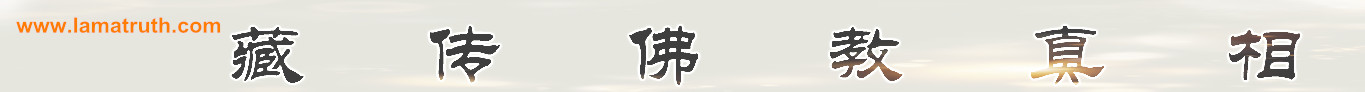请问阿赖耶识是真实有吗?
答:阿赖耶识亦名阿陀那、所知依、如来藏、真心、真如、法界实相、万法根源...等异名同义。即然是真心当然就是真实而有。若无真实心,一切有情死后就成断灭。成断灭见故不符佛旨。
那跟三法印中诸行无常有没有违背?
答:阿赖耶识并不与三法印相违背。「诸行无常」指的并非是阿赖耶识的心行,而是说众生的身行口行意行,也就是由色阴与受阴、想阴、识阴四阴所构成的「行阴」的体性是无常生灭,没有任何一个行阴是可以常而不灭。
若说诸行不包括阿赖耶识?那再阿含经中有何依据?
答:「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并不包括阿赖耶识的心行」,在阿含经中有没有类似这段文字记载,我并不清楚,因为我没空去找阿含经文中完全相符的某一段文字。我们只是如实理解阿含经中的三法印在讲什么。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去逆向思考:阿含经中有没有依据可以证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包括了阿赖耶识」?那如果阿含经中找不到一段「完全相符」的经文,那任何学术界的学者教授是不是也不可主张说「阿赖耶识是包含在诸行无常之中」?
其实不必依经典就可以推论阿赖耶识不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之中,因为现象界不外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超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没有法可言。若问这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有哪一个蕴?哪个处?哪个界是在讲阿赖耶识? 或者说你要把阿赖耶识要归类在哪一界?哪一蕴?哪一处? 如果你不能把阿赖耶识成功的归类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中,那就可以证明阿赖耶识并非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所涵摄。即然阿赖耶识不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所涵摄,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讲的义理就不包括阿赖耶识,而是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诸行无常、诸行无我。
但是如果像印顺法师断章取义,只取阿含经的虚妄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也不行,因为只有二法印没有三法印,那阿含法就不圆满也不如法。所以第三个法印才是阿含经的真实法--「涅槃寂静」,这就是在讲阿赖耶识的自性是不生不灭,是涅槃性、是本来就寂静,非因修得而寂静;何谓涅槃?涅者不生、槃者不灭。如是三法印涵盖虚妄法与真实法,这样佛法才能行于中道而不致堕入断常二见中。如果像印顺为了要掩饰其堕断见外道,却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含摄的虚妄心-第六意识拿来建立为第三法印(真实法)-「涅槃寂静」的主体,那又堕入了常见外道之中。因为把虚妄法拿来当作真实法,这就是佛法中所破斥的常见外道、心外求法者。因此学术界有人评论印顺的主张其实是同时俱足断常二见的原因。
*(未完待续....以上言论只是个人自心流露的见解,并未翻阅经典或别人的着作。因为阿含只是很粗浅的佛法,并不难懂,却因为被印顺弄得很複杂。如果有人把简单的法搞得很複杂难懂,这就不是善知识。)
续.....
阿赖耶识跟印度教的梵有何不同?
答:佛教的第八识阿赖耶识是法界实相之真实心,是可知可证的法。而印度教的梵我思想,是玄学,是不可知不可证的意识心妄想法。
在印顺法师的着作《印度佛教思想史》中,第169页~170页中说:
『佛法说无我,而现在极力说如来藏我,到底我是什么?《大般涅槃经》说: 『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者,是名为我』。这与奥义书所说我,是常、是乐、是知,似乎相差不远。』
复次,印顺法师的着作《华雨选集》中,第75页说:『「如来」有神我的意义,胎「藏」有『梨俱吠陀』(注:婆罗门教的经典四吠陀之一)的神话渊源,所以如来藏、我的思想与传统的(「佛法」与「初期大乘」)佛法,有着相当的距离。…。如来藏说,有印度神学意味,而教典的传出,正是印度教复兴的时候;如解说为适应信仰神我的一般人的方便,应该是正确的!』
复次,在『华雨选集』中,第94~95页中又说:『如「后期大乘」的如来藏、佛性、我,经说还是修菩萨行的。如知道这是「各各为人悉檀」(注:观众生根器不同,而为其所施设的方便法门),能顺应世间人心,激发人发菩提心,学修菩萨行,那就是方便了。如说如来藏、佛性是真我,用来引人向佛,…,那就可以进一步而引入佛法正义了。只是信如来藏我的,随顺世俗心想,以为这才是究竟的,这可就失去「方便」的妙用,而引起负面作用了!』
以上是印顺法师在其着作中,认为佛说三转法轮经典:《大般涅槃经》及诸多方等唯识经典中,所说如来藏之常、乐、我、淨,与婆罗门外道『奥义书』中所说之梵常、梵乐、梵我、梵淨,是『似乎相差不远』! 印顺法师亦认为,如来藏我之思想,是『各各为人悉檀』,是佛陀为渡梵我外道而施设之方便法尔,故非是究竟、真实、可证之法;所以印顺认为,『如来藏』三个字拆开来,说『如来』有外道『神我』的意义,『藏』与『吠陀』、印度神学之神话思想有着渊源。
复次我们来看看《奥义书》所说的梵我思想及其源起:
(1)源起:
印度哲学史的发展由婆罗门思潮(Brahmanism)、沙门思潮(Śrāmaṇism)及世俗思潮(Secularism)三大体系所构成,以婆罗门思潮之吠陀(Veda)传统为正统,而以吠檀多学派(Vedānta)为主流代表。其中,婆罗门思潮与沙门思潮二者之关係,实为印度哲学史及印度文化史之大事,亦即,此两大哲学思潮为印度哲学之主要内容。
古印度吠陀时期(大约西元前1200~600年)分为早期及晚期,古奥义书属吠陀晚期。古奥义书年代之有其确认之困难,但一般学者认为古奥义书之时期大约为西元前800~300年之间,而新奥义书约为西元前300年以后所成立之;由于新奥义书并无甚么哲学价值,因此一般所谓的奥义书即是指古奥义书。
古奥义书由不同时代不具名之多数思想家编撰所成,因此,具有多种不同之思想,甚至有所矛盾,有关沙门名称、沙门思想或佛陀、佛陀思想,并未见于其书中。在古奥义书内容主要讨论人的自我、宇宙本体、此两者之关係、业力轮迴、瑜珈及解脱,这些概念、学说等,奠定了后世婆罗门之哲学思维方针及其思想。
《奥义书》是印度婆罗门教的最重要的修行经典之一,浓缩了四部吠陀论的精华,是一个论文集,有一百多篇,其中最重要的有五十篇,《奥义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Vedanta,汉译为《吠檀多》,Vedanta就是对《吠陀》的最终、最高的阐释。在奥义书中,认为世界之全体皆由造物主(大自在天、梵天、摩醯道首罗天)所造,而人为世界之一部份,不能外于或脱离于造物主。人之身终将而死,故唯有透过对造物主之认知,人之精神可恆常不死。
(2)梵我思想:
在晚期奥义书进一步地说明,一切的自我感官及其客观的自我认知,皆是至上且恆常之『阿特曼』(梵)(Brahman)所支持。人由于经由感官向外追求感官之乐,故不知其真正之自我(梵)。一般的有情众生,经由感官而向外寻,故人向外追逐而不知向内探寻其内在自我,因而步入生死之苦。由于人不知色、味、嗅、声、触之辨别,亦是由于梵的自我。因此,为知此自我,人必须首先控制感官,唯有具有此认识之人,且善于驾驭其感官及意且清淨者,此人修行到像毗溼奴神(Viṣnu)之境界则解脱不再流转生死。一切均是梵(Brahman),而此阿特曼即是梵。
(3)梵我与气息之关係:
在早期奥义书中,已明言『气息』(prāṇa,意指生命之涵义),即人之呼吸,优于感觉器官及活动器官。所以者何?因当气息离去四肢及身时,人将枯竭而死。因气息为维繫生命所需之机能,因而将其意义加以演绎而视之为人之本质。所以奥义书中把人身有五种气息:气息(入息)、出息、周遍息、上息、均等息,但这五种气息,事实上只是同一气息之不同作用尔。气息与阿特曼(梵)有重要之关係,但阿特曼(梵)则更加重要。
在后期奥义书进一步阐明有关『气息』优于语及意之优越地位。最初将气息解释为人之生命,但主张气息并非阿特曼。气息是由阿特曼所生。由于人的行为活动由前生的意活动所驱使,故气息与人身发生关联,且将其本身分成人身之五种气息而作用之。其中入息存于眼、耳、口、鼻;出息存于排泄及生殖器官;周遍息存于游动于与心脏相连之脉道中,而阿特曼(梵)即位于心脏中;其中之一脉向上且经由它,上息或经由善行导向善世界,或经由恶行导向恶世界,或经由善行亦恶行而导向人之世界。
(KC评:奥义书梵我思想认为吾人之『真我』-阿特曼(梵),包藏于心脏之中;此种思想,亦如西藏密宗之一派:『佛法心中心』-元音老人之所说完全相同,其着作《心地法门-恒河大手印》第219页中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按密宗的理论讲,第八识-阿赖耶识,就在心包里,有两条脉管脉从后面连通心包和眼睛。密宗观光修行,外光由眼睛打进去,将我们自心本具的法性光激发出来。』;是故西藏密宗的自性真我之思想。其实才是与外道奥义书梵我思想之合化。)
在奥义书中,气息不仅为物理的、生物的机能,且是个人之生命及为宇宙之生命。气息因而甚至被视为阿特曼、梵。但整体而言,奥义书思想家并不认为气息为阿特曼、梵。因气息受限于醒及梦状态,既为有限,则气息不可能为真正之自我。
(4)梵我与意的关係:
早期奥义书已认为『思虑』为『意』机能,且认为意并非外部或内部感官,而视之为自我之一种意向,且所採用的两种自我概念(有限或无限、二元或一元),取决于思虑的基础是否是行为活动或知识(指阿特曼及梵之知识)虽然自我本质上为无限,但因它被吾人等同于意,且以意享用欲望,故自我受限。但一但人知自我即是梵,他成为无限且离于欲。此种梵概念才是吾人所当享用者。如同梵为万物之本质,它又称为心脏,因心脏为人身之中心且为自我之所在,但意既非万物之本质,也非自我之所在。后期奥义书说明,自我本质上是无限且同于梵,但经由它与意及为意活动所驱使的行为活动发生关连,因而有了有限之形体。意作为一种意向而有所思虑,因而意是不定且难以控制。若不能驯服意,人不能离于轮迴。但若有认识,且感官及意均已驯服且清淨,人将至毗湿奴神之处且脱于轮迴。
(KC注:以上(1)~(4)点内容,参考『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五期)之《古奥义书与初期佛学关于人的自我概念之比较与评论》(作者为真理大学宗教系讲师-林煌洲先生))
KC评论:
末学参考多方的资料,简单地将这诸多法义冲突的婆罗门教之梵我思想,稍作整理,其根本教义,主要分成有三种:
(1)崇奉四吠陀论、奥义书,谓其诵论之声音、咒音,为诸法实义之梵王声,故是为『常、乐、我、淨』,其他声音不契实义,则为『无常、苦、非我、不淨』者。
然而类似以此声音、咒音,作为诸法实相者,现在比较有名气的外道有印度锡克教、台湾的清海无上师等(其所说之观音法门,是以静坐中专注在耳根、声尘、耳识上,聆听天上的美妙声音以为究竟实相之法)、及西藏四大派喇嘛教:红、白、黄、花教(其以观想种子字及其咒音,以为诸法实相,藏密创造诸多伪经之一的『大日经』卷五曰:『所谓阿字者,一切真言心,从此遍流出,无量诸真言,一切戏论息,能生巧智慧。…,阿字名种子,故一切如是,安住诸支分;如相应布已,依法皆遍授。由彼本初字,遍在增加字,众字以成音,支体由是生,故此遍一切,身生种种德。』)
复次,以声音、咒音为诸法实相之外道思想,早已被佛陀破斥为『声论外道』者,其以耳根、声尘、耳识为实相法,皆落入十八界之虚妄法中,非是三界诸法实相之义理也。
(2)梵我思想以为神我说其原因,而产出一个原体「梵」Brahman之思想。因世界之开发生成,发现此唯一之「梵」自行繁殖之意志,遂造有世界万物。他们的解脱方法,认为在于『生活精神』(迷我)与『最上精神』(梵我),两者之差别,在于爱取贪着之深浅差别也。
若个人受迷惑之『生活精神』,若能了知其自性时(指精神、灵魂,非佛法之如来藏),则得与『最上精神』之『梵』合而为一,即是究竟解脱矣。而此种思想与藏密的颇哇法、迁识法非常相似,其认为:行者可于平时或临终之时,妄想本尊住在空中,妄想自身中脉之明点,从头顶梵穴冲出,与所观想之本尊合而为一,将行者之明点(藏密妄想的真实心、法身)与佛法身相互结合,带到淨土去;是故与梵我外道有着相同的看法。)
(3)梵我外道,是以为梵天(摩醯首罗天,或称大自在天)为出生世界之太原,于三界中所有一切,有情、无情皆是摩醯首罗天所生。摩醯首罗之全身者:以虚空是头、日月为眼、地是身、水是尿、山是粪、一切众生是腹中虫、风是命、火是煖、罪福是业、皆是摩醯首罗之身体也。此种思想与一神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一贯道之思想极其类似,其皆认为一切有情、无情、世界宇宙,皆是上帝、阿拉真主、无始天尊、无极老母所创造的。以为只要符合上帝的期望就可以在死后回到上帝的怀裡,或者是与上帝合而为一。
复次,从佛陀对梵我外道思想的邪见,可以在《大般涅槃经》见到一些端倪 ,在卷19曰:《今有大师,名迦罗鸠驮迦旃延(摩醯首罗论师),……,为诸弟子说如是说:
『若人杀害一切众生,心无惭愧,终不堕恶,犹如虚空,不受尘水,有惭愧者,即入地狱,犹如大水,润湿于地,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瞋,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为作,云何当言人有罪福?』》
如是梵我外道婆罗门论师之所言,严重误导众生,妄造诸恶业,其邪见之可恶,印顺法师却将此邪恶之梵我外道思想,与慈悲、清淨的佛教溷为一谈呢?甚至与佛说《大般涅槃经》之如来藏法溷为一谭呢?
复次,末学要请问印顺法师:『如果《大般涅槃经》是外道梵我思想之合化,那为何在《大般涅槃经》中,看不到讚美梵我外道或其论师之思想呢?反而却是在破斥梵我外道论师之邪思邪见呢?』 如是印顺邪师,居心叵测,以刻意毁谤大乘佛说如来藏法为非佛所宣说,诬指为是梵我外道思想之合化,来溷淆全球佛教之学人,严重遮障众生之法身慧命,是故吾等学佛之人,不可不慎也!
接下来谈谈佛说如来藏之『常乐我淨』:
(1)请先参考《大般涅槃经》 (卷39):
《 佛言:『善男子!凡夫不能思惟分别如是事故,说言有我,及有我所、我作、我受。』
先尼言:『如瞿昙(佛)说无我、我所,何缘复说常、乐、我、淨?』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说内外六入及六识意常、乐、我、淨。我乃宣说灭内外入所生六识,名之为『常』,以是常故名之为『我』,有常我故名之为『乐』,常我乐故名之为『淨』。善男子!众生厌苦断是苦因,自在远离是名为我,以是因缘我今宣说常、乐、我、淨。』 》
如是佛所说之『常乐我淨』,非是以六根、六尘、六识为『常乐我淨』,而是离于十八界的『常乐我淨』──如来藏也!此是从理上来说;若从事修来说,唯究竟佛地才能真常、真我、真乐、真淨。
然而印顺法师,不知不解佛所说之大乘如来藏『常乐我淨』之义理,不知解如来藏即是『胜义谛』、『第一悉檀』,亦不知不解,佛说二乘法之『苦、不淨、无常、无我』,实是『俗谛』、是『对治悉檀』、『为人悉檀』,是对治佛弟子对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之我见及我执,所施设之方便法也,所以印顺法师以其小乘根性,妄说大乘佛法,竟以佛学泰斗而自居,误人慧命,犹如小娃儿开大人车一般地危险,是故《首愣严义疏注经》 (卷7)曰:【由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足。无上觉道如宝所,小乘涅槃如化城,但恋权乘,不求究竟,得少为足,故发尘劳。】
复次,佛于《大般涅槃经》(卷二)中,开示二乘俗谛与大乘胜义谛之不同义意:
《 『无我』者即『生死』, 『我』者即『如来』。
『无常』者『声闻缘觉』,『常』者『如来法身』。
『苦』者『一切外道』, 『乐』者即是『涅槃』。
『不淨』者即『有为法』,『淨』者『诸佛菩萨所有正法』。 》
再请参考《大般涅槃经》 (卷2):
《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谛听谛听!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达其义,何等为义?如彼醉人见上日月,实非迴转生迴转想,众生亦尔,为诸烦恼无明所覆,生颠倒心:我计无我、常计无常、淨计不淨、乐计为苦,以为烦恼之所覆故,虽生此想不达其义,如彼醉人于非转处而生转想。
『我』者即是『佛』义,
『常』者是『法身』义,
『乐』者是『涅槃』义,
『淨』者是 『法』义;
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贡高流转生死?
汝等若言:『我亦修习无常、苦、无我等想。』是三种修无有实义。
我今当说胜三修法(佛说有胜过于苦、无常、无我之四种修法)
『苦者计乐』、『乐者计苦』,是颠倒法。
『无常计常』、『常计无常』,是颠倒法。
『无我计我』、『我计无我』,是颠倒法。
『不淨计淨』、『淨计不淨』,是颠倒法。
有如是等四颠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诸法。汝诸比丘,『于苦法中而生乐想』,『于无常中而生常想』,『于无我中而生我想』,『于不淨中而生淨想』;世间亦有常、乐、我、淨,出世亦有常、乐、我、淨。
世间法者有字无义,出世间者有字有义,何以故?世间之法有四颠倒故不知义,所以者何? 有『想颠倒』、『心倒』、『见倒』,以三倒故,世间之人『乐中见苦』、『常见无常』、『我见无我』、『淨见不淨』,是名颠倒,以颠倒故,世间知字而不知义。
何等为义?『无我』者即生死,『我』者即如来,『无常』者声闻缘觉,『常』者如来法身,『苦』者一切外道,『乐』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为法,『淨』者诸佛菩萨所有正法,是名不颠倒,以不倒故知字知义,若欲远离四颠倒者,应知如是常、乐、我、淨。 』》
以上由佛之开示可知,外道、凡夫、印顺邪师等人,不知、不信、不解佛所说之如来藏『常乐我淨』真实法,只知其名字而不知其义理也;彼众因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故,而妄解佛说『常乐我淨』之真实义,而诬谤真实、可知、可证之法-如来藏,为不可知、不可证、虚构之梵我思想之合化,犹如世间愚痴人之颠倒想,以『乐中见苦』、『常见无常』、『我见无我』、『淨见不淨』之邪见者,如是称为:知『常乐我淨』之字,而不知『常乐我淨』之义也。
是故各位再回想一次看看!印顺法师说:『佛法说无我,而现在极力说如来藏我,到底我是什么?《大般涅槃经》说: 『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者,是名为我』。这与奥义书所说我,是常、是乐、是知,似乎相差不远。』末学摘录以《大般涅槃经》之内容,作为互相比较:
(卷七)曰:
《善男子!若人不闻如来甚深祕密藏者,云何当知有佛性耶?何等名为祕密之藏?所谓【方等大乘经典】。善男子!有诸外道,或说我常,或说我断;如来不尔,【亦说有我】,【亦说无我】,是名【中道】。》
如是印顺不知如来说【无我】及【有我】之中道义理,亦不知古印度之婆罗门梵我外道思想之义理,更不知佛陀于成道时,最初因观察众生根器尚不成熟,存在着过去于婆罗门教中,所薰习之四吠陀及奥义书的梵我思想,故知弟子尚无法分辨『梵我』与『如来藏我』之差异,故于初转法轮(阿含)时期,先为钝根初机人及二乘人宣说『无我』等法,主要在开示众生之五阴十二处十八界,是集众苦之因(苦)、是空相不可得(空)、是无常生灭法(无常)、非是真实之我(无我);以『无我』法破除当时之梵我思想,及其它常见外道之我见、我执;如是佛陀为不令因缘不俱者,在听闻第一义谛真实我-如来藏后,而落入外道常见中,与梵我外道互相溷淆,是故阿含经隐覆真实我-如来藏,而说『无我』法;又为弟子在听闻『无我』法后,不致落入外道断灭见中,而说有个实际的『涅槃本际』。
再者,佛为二乘人隐覆如来藏,而说无我法。故于《大般涅槃经》 (卷5)曰: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世尊有祕密藏。」是义不然!何以故?诸佛世尊唯有密语,无有密藏。…,云何当言诸佛世尊有祕密藏?』佛讚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来实无祕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满月处空显露,清淨无翳人皆睹见,如来之言亦复如是,开发显露清淨无翳,愚人不解谓之祕藏,智者了达则不名藏。…。
如来视于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教一子者谓声闻弟子,半字者(喻小乘),谓九部经;毘伽罗论者(喻大乘),所谓方等大乘经典;以诸声闻无有慧力,是故如来为说半字九部经典(小乘经典),而不为说毘伽罗论方等大乘。善男子!如彼长者,子既长大(喻信心福德智慧具足者),堪任读学,若不为说毘伽罗论(喻大乘),可名为藏(暗藏不教授),若诸声闻有堪任力,能受大乘毘伽罗论(信受方等经典),如来祕惜不为说者,可言如来有祕密藏(若如来因吝惜,不为有信心福德智慧之声闻人宣说大乘方等经者,汝可谓如来有祕密吝藏之法而不教者);如来不尔,是故如来无有祕藏。如彼长者教半字已,次为演说毘伽罗论(先教完基础简单的法,若能了解信受后,再教深奥难法)。我今亦尔,为诸弟子说于半字九部经已(说完小乘法)。次为演说毘伽罗论(再教大乘法)。所谓如来常存不变(方等经之如来藏常、乐、我、淨也)。》
复次,佛于不同时间地点宣说阿含经,前后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待至众生根器因缘俱足时,于二转法轮(般若)时期,为菩萨种性者,宣说大般若经,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如来藏的种种体性…等,前后又花了二十二年,如是渐进,再于三转法轮(方等)时期,为利根者宣说方等唯识经约八年的时间,开示如来藏之所含藏种子之功能差别及无明烦恼等,最后于涅槃前,宣说法华经、大般涅槃经约八年时间;佛陀前后说法,总共花了四十九年的时间,最后在拘尸那城,阿利罗跋提河边,于双娑罗树中间入涅槃。印顺法师,不知其义,以初转法轮阿含经之俗谛-『无我』法,来推翻二转法轮以后,佛说大乘般若胜义谛-『如来藏』法;印顺法师犹如一般小学生(小乘)的数学程度,只懂加四则运算淢乘除法(四圣谛),而不懂大学生(大乘)的工程数学-微积分(般若、唯识),而大肆否定大学生的微积分为非数学法(非佛法、是梵我外道法)。
如是吾等末法时期之正信佛弟子们,不应随从印顺邪师邪见,跟着否定二乘佛法、及大乘佛法之根本-涅槃本际、如来藏、阿赖耶识;或随顺其邪师,将佛说如来藏我,诬指为为奥义书梵我外道思想之合化。是故佛于《大般涅槃经》(卷第七)曰:
《若有说言如来为欲度众生故说【方等经】,当知是人【真我弟子】。若有【不受方等经者】,当知是人【非我弟子】,不为佛法而出家也!【即是邪见外道弟子】,如是(认同大乘方等)经律,是佛所说;若不如是(而谤方等经者),是魔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复次,外道凡夫因为诸无量烦恼及无明所覆障,使意识心生起颠倒想故,于我中计无我想、于常中计无常想、于淨中计不淨想、于乐中计为苦想;犹如印顺不知不解佛所说之如来藏『常乐我淨』及外道『常乐我淨』之分际,以生无明颠倒想,妄将《大般涅槃经》及诸方等唯识经论之如来藏『常乐我淨』,与外道婆罗门教之梵我思想《奥义书》所说之『常乐我淨』溷为一谈,印顺个人因未在实修上下功夫,故无实际之证量,却以粗糙之历史考证方法,及其护持西藏喇嘛黄教-应成派之私心的前提下,以一句『似乎相差不远』、『不究竟』、『方便法』之说,来否定佛于般涅槃前,所说的最后一部大经-《大般涅槃经》及所有的方等唯识经论。
复次,印顺法师为何否定《大般涅槃经》?
印顺法师之所以会否定《大般涅槃经》及一切佛说大乘经典,在于印顺本人终其一生,仅在佛经文字中鑽研法义,从未以念佛法门、或以禅宗法门做为实修实证,是故未能真悟本心实相,不见佛性,不能解行相资,不能宗教互通;印顺的思想,以离如来藏而说:『一切法空、缘起性空』,来否定一切有关佛说如来藏之经典,而认为阿含经典之『一切法空、缘起性空』之无我思想,才是究竟义理,并于其着作中公开宣称『大乘法非佛说』,呼吁佛弟子要『回归佛陀的本怀』,以佛说小乘阿含经系为根本依,将佛说大乘如来藏思想,斥为是佛教后期演变,认为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陀的永恒的怀念』,而集体创作之伪经,故印顺法师认为,如来藏思想是外道梵我思想之合化,又将佛说如来藏法之因缘,诬指为是佛为引渡梵我外道者,而施设之方便尔。
然而,印顺法师大肆否定一切如来藏经典,其认为阿含经系才是佛陀亲口所宣说之法,认为阿含经亦无如来藏之说,因此大力呼吁佛弟子要『回归佛陀的本怀』,依止藏教四阿含经典为佛教之根本,来加以驳斥大乘如来藏法,诬指为梵我外道之演变合化;如是印顺法师近数十年来,以其在佛教中的地位、名声、势力,以其着作等身的信心,就以为可以一手遮天,笼罩全球佛教界人士,然而关阿含经可证明早就有出现如来藏、大乘、方广、真实如来等,其实是与大乘如来藏法相互贯通一致。
跟一般说的灵魂或灵性有什么差异?
答:在中国的民间信仰裡,灵魂是指人死后的鬼魂或中阴身,或是说人之所以不死是因为有灵魂住在身中。所以从民间信仰或道家的信仰裡,灵魂是可以在某些因缘下见到的,例如阴阳眼或亲人在梦中所见。而灵性就是说人的见闻觉知,也包括情感部份。只是有形的灵魂或是心灵的灵性,包括一神教所说的灵性、灵魂思想,或是印度教梵我思想,这都是不离五阴十八界的有为有漏境界法,都是不离虚妄的意识境界。而一切有情身中的第八识-阿赖耶识是超越意识境界、超越五蕴十八界,亦超越三界六道轮迴。因为阿赖耶识无觉无知,没有情感没有喜怒哀乐,没有色、声、香、味、触,亦不在欲界,不在色界,不在无色界,衪不在三界内,也不随六道而轮迴,但却能出生灵魂、灵性....等,可是衪却不是灵魂,也不是灵性。那阿赖耶识到底住在何处?阿赖耶识住在自己的境界中,也就是涅槃中。至于涅槃为何?不妨多读几遍心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