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me » » 評論南傳佛教上座部及印順法師 |
太虛大師對印順邪師的評議 |
太虛大師對印順邪師的評議
圍繞《印度之佛教》一書展開的往復論諍,是反映師徒倆多方面矛盾的一個窗口。雖然這本書是印順較早期的作品(年近不惑),但已集中宣示了他的佛學思想和治學之道。(在後來的著述中,印順多次自得地引述該書的話,並於《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中說:“現在來看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的舊作,當然是不會滿意的!然一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對於我的作品,應該是最重要的!假如這是大體正確的,那敘述與論斷,即使錯誤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釆。”)1942年,印順法師將此書第一章鈔寄與太虛大師,請為之序,大師隨即寫就《議“印度之佛教”》予以略評,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公平看法”。印順出版全書時附了一篇《敬答“議‘印度之佛教’”》,為自己辯護,結果招來上師更加嚴厲的駁斥。太虛大師的《再議“印度之佛教”》加大了批判的力度,並於1943年8月30日向漢藏教理院全體師生做了公開演講。在上師的據理斥責下,執弟子禮的印順不得不有所收斂。
從這個角度看,太虛大師1947年的示寂,對印順來說不是個壞消息。於是,在嗣後的漫長歲月中,一套曾受其精神導師嚴厲斥責的治學之道和錯誤觀念,便有了機會讓中國佛教徒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方能觸及真理。
在《再議“印度之佛教”》中,太虛大師針對印順佛學研究和歷史考證的方法與觀點,提出了批評。大師指出,企圖從小乘經論中尋求大乘源流的做法甚不可取,“亦因此陷近錫蘭之大乘非佛說或大乘從小乘三藏紬譯而出之狹見”。對於“大乘非佛說”,太虛大師的態度是鮮明而堅決的:“大乘經源出佛說,非非佛說,亦非小乘經論紬釋而出。”作為一位具有純潔的宗教信仰的大乘佛教徒,太虛大師顯然是將一切佛法均當作佛陀不思議內證境界的任運流布來敬重,而不是如《印度之佛教》的作者那樣,把神聖玄秘的教法、教史均視為完全可由凡夫分別心加以懸想計度的世間普通學問對待。
對於印順僅承許在阿含中能找到根據和隱喻的教法的偏執,太虛大師據理駁斥道:“原著第三章佛理要略,僅列世間之淨化,世間之解脫兩表;而菩薩道一表,則列之第十一章第三節末,意許錫蘭傳大乘非佛說,以大乘為小乘學派分化進展而出……或余他處所謂五乘共法與三乘共法,而特大乘法則竟未為承受。故雖特尊龍樹亦不能完全宗奉,而有‘已啟梵化之機’之微詞;所余大乘經論不為所尊重,復何足訝!其附攝大乘於小乘,不容有超出小乘之大乘,自當與大乘佛菩薩立場有異。”大師於此尖銳指出,印順其實是假弘菩薩精神、龍樹學說之名來貶毀大乘真義,骨子裡正是不折不扣的“大乘非佛說”邪見的信徒。
——如果讀懂了如來藏系經論裡深刻隱寓著的離戲空義,讀懂了勝義法界在空分和現分上的圓融一味,那只會倍感欣暢,而絕不可能對空性或顯現的任一方畏若洪猛視作仇怨。在智者面前,脫離了顯現的空性和脫離了空性的顯現,同樣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印蕭邪說的狹隘偏墮,不過是習慣做二元對立的分別、取舍的凡夫心所玩的騙人把戲而已。把凡夫心的運作特征無限類推到勝義法界中去,怎麼可能不出問題呢?
既然所謂的“龍樹傳人”和“大乘孤子”,在雙運離戲實相面前都栽了跟頭,那我們當然不奢望一干世間學者專家,能比他們做得更出色。拋掉了空性靈魂、完全由凡夫實執分別心當家的純學術性佛教研究,能否觸及佛教的本質並取得終極裁判權,也就很成問題了。
印順《敬答“議‘印度之佛教’”》中的一段話,表明了他對大乘佛教的基本態度:“菩薩乘為雄健之佛教,為導者,以救世為己任者,求於本生談之菩薩精神無不合。以此格量諸家,無著系缺初義,《起信論》唯一漸成義,禪宗唯一自力義,淨之與密,則無一可取,權攝愚下而已。”可見大乘佛教在他眼中幾乎一無是處,即便略為可觀的“菩薩精神”,也概莫出於小乘經的本生行跡之外。
針對印順對大乘諸宗的批評,太虛大師反評道:“令眾生都脫苦安樂而發菩提願,忘己為他,不求自利,大悲為根,大乘所共,安見無著系之缺此?起信不限時劫,華嚴短劫亦入長劫,禪宗頓悟不廢漸修,天台六即尤解圓行漸,豈必違任重致遠精神?……”兩股不妥協的力量繼續猛烈碰撞。
印順法師對印度佛教歷史分期的看法,也引起太虛大師的不滿:“惟於佛世以來之教史,似因莊嚴‘獨尊龍樹’之主見,將大乘時代揉成離支破碎,殊應矯正”、“‘獨尊龍樹’,乃前沒馬鳴而後擯無著,揉成支離破碎也”、“原著於此千五百年中乃在馬鳴後、無著之前短短百余年為龍樹提婆獨立一時。馬鳴為大乘興印度之本,抑令湮沒,無著與密教極少關系,乃推附後時密咒為一流;約為第一時六百年,第二時一百年,第三時八百年,則除別存偏見者,無論何人難想其平允也。”表面在推重中觀,甚至不惜為此犧牲大乘佛法的整體圓融,但是,倘若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大乘佛法均來源不淨、疑偽重重,在此嚴竣情勢下,喪失了背景依托的龍樹學說又怎能安然無恙呢?太虛大師所謂“故雖特尊龍樹亦不能完全宗奉,而有‘已啟梵化之機’之微詞”,就非常客觀地指出了印順在這上的兩面性。在將他尊為“導師”的台灣,以“佛教徒”身份攻擊龍樹菩薩、誣謗大乘佛法的行為蔚然成風,很難說這裡面沒有他的一份“功勞”。
《印度之佛教》還將印度佛教的衰亡歸咎於討厭的“真常唯心論”(如來藏學說),太虛大師對此亦有不同意見,甚至針鋒相對地說“令印度佛教衰滅,除外來政治社會原因外,咎莫大於此執空諍者。”譏諷之意溢於言表。
|
| Home » » 評論南傳佛教上座部及印順法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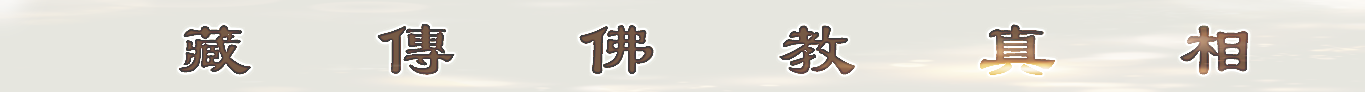
简体 | 正體 | EN | GE | FR | SP | BG | RUS | JP | VN 西藏密宗真相 首頁 | 訪客留言 | 用戶登錄 | 用户登出
- 評論南傳佛教上座部及印順法師
- 喇嘛教本質的海濤法師放生爭議
- 雙身法黃教祖師--宗喀巴(廣論)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淨空法師揭發邪惡之偽藏傳佛教開示輯
- 慧律法師破斥藏傳假佛教及「人間佛教」之邪說
- 淫人妻女之活佛喇嘛(偽藏傳佛教)性侵害事件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六字大明咒秘密大公開
- 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性醜聞
- 高僧學者名人批判雙身法之西藏密宗(偽藏傳佛教)證據大公開
- 藏密本質的聖輪法師性醜聞事件簿
- 雙身法達賴喇嘛秘密大公開
- 殘暴的偽藏傳佛教、西藏密宗、喇嘛教殺人證據
- 宗教性侵防治文宣教育(歡迎流通)
- 雙身法喇嘛教(西藏密宗、偽藏傳佛教)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紅教祖師--蓮花生(大圓滿)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白教祖師--密勒日巴(大手印)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真心新聞網、各家宗教新聞
- 漫畫-密宗活佛、喇嘛、仁波切
- 喇嘛教雙身法連載專欄:台灣玉教室
- 偽藏傳佛教雙身法分享專欄:-讀者來鴻
- 罪惡達賴 罪惡時輪
- 偽藏傳佛教(藏密)問答錄●學密基本常識
- Swami瑜伽性侵大師
- 人面獸心-索達吉堪布雙修大揭密
- 國學大師-南懷瑾雙修大揭密
- 卡盧仁波切雙修大揭密
- 索甲仁波切雙修大揭密
- 真佛宗盧勝彥雙修大揭密
- 破斥藏密多識喇嘛《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 陳健民上師講述如何修學密宗邪淫男女雙修灌頂
- 剖析天鑒網悲智版主愚癡言論輯
- 嗜血啖肉的人間羅剎---喇嘛教絕非佛教
- 嗜食糞尿精血等穢物的藏傳佛教
- 附佛外道-法輪功的秘密
- 揭發「藏傳佛教」轉世活佛的騙人內幕
- 認識真正善知識-蕭平實老師
- 偽藏傳佛教詩詞賞析
- 第一部揭開西藏神秘面紗的大戲--西藏秘密
- 破斥遼寧海城大悲寺妙祥法師抵制正法
- 破斥一貫道
- 破斥瑯琊閣
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當地已有民間信仰的“苯教”流傳,作法事供養鬼神、祈求降福之類,是西藏本有的民間信仰。
到了唐代藏王松贊干布引進所謂的“佛教”,也就是天竺密教時期的坦特羅佛教──左道密宗──成為西藏正式的國教;為了適應民情,把原有的“苯教”民間鬼神信仰融入藏傳“佛教”中,從此變質的藏傳“佛教”益發邪謬而不單只有左道密宗的雙身法,也就是男女雙修。由後來的阿底峽傳入西藏的“佛教”,雖未公然弘傳雙身法,但也一樣有暗中弘傳。
但是前弘期的蓮花生已正式把印度教性力派的“双身修法”帶進西藏,融入密教中公然弘傳,因此所謂的“藏傳佛教”已完全脱離佛教的法義,甚至最基本的佛教表相也都背離了,所以“藏傳佛教”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喇嘛教”也就是──左道密宗融合了西藏民間信仰──已經不算是佛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