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me » » 認識真正善知識-蕭平實老師 |
稱呼別人為菩薩,不知有無犯大妄語? |
稱呼別人為菩薩,不知有無犯大妄語?
請問kc師兄,那我們也菩薩來菩薩去的稱呼,不知有無犯大妄語?因我看完你po的楞嚴經卷六內心起了很大的困惑和恐懼。
kc答:
末學就以《 楞嚴經之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的摘錄內容作為說明: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
這經文中就與大勢至菩薩同修念佛圓通法門的菩薩,有無量無數同時參與楞嚴盛會,而由五十二位菩薩為代表,偕同大勢至菩薩頂禮佛足,再由大勢至菩薩說出此一念佛圓通法門。
何以由五十二位菩薩代表而不用其他的數目呢? 此中具有很深的含意:這一句表明了此種法門之可淺可深,利鈍兼收。從最淺的凡夫菩薩--初信位開始到十信圓滿,及賢位菩薩--十住位、十行位、十迥向,上至聖位的初地至十地, 乃至即將成佛的等覺妙覺位菩薩等,無量無數,皆同修此念佛圓通法門。**菩薩,經典中十信位的佛弟子都可以稱為「菩薩」了,為什麼汝等不允許自己或其他初住位乃至二住、三住、四住的眾生互稱為菩薩呢?還是汝要把具有菩薩性的眾生,或是想發心修學菩薩道的眾生,活生生的推往聲聞乘或獨覺乘的死胡同呢?汝對於菩薩稱呼之不解,甚至反對他人互稱菩薩者,是為汝之大過失。
所以「菩薩」這個稱號,是可以遍及各種不同位階的凡夫眾生,不唯是已證悟的「賢位」菩薩,或是入地的「聖位」菩薩。此外,佛弟子經常有些稱號濫用無度,亦有大過失。 即若無實質意涵的名稱則不可亂用,汝等應當知悉。例如:大師、法師、尊者、大菩薩、活佛、禪師、法王、法主、導師、上人....等皆不可亂用,否則會有成就他人大妄語之共業。 何以故?隨舉「法師」一例:
一般出家受具足戒的人,古代都稱為比丘或僧,未受具足戒者稱為沙彌或沙彌尼。但現今人看到剃著光頭的比丘或沙彌,倒頭就拜為「XX法師」如是愚癡無智之佛弟子,濫用「法師」名號,不但有令對方造成大妄語之嫌,亦貶低真正「法師」身份,彼等毫無實質意涵之虛偽法師如何能與古德真正精通經、律、論之「三藏法師」齊名?又何德何能可稱名為「法師」耶?
然法師的定義請參考以下文獻:
「法師」,梵語dhamma-bhanaka,巴利語dharma-kathika,又稱為「說法師」,泛指通曉佛法又能引導、教化眾生修行之人。《妙法蓮華經玄贊》中說:「可軌可持,名之為法,可習可範,目之為師。此教可軌,此理可持,雙名為法。此法可習名為法師。」(大正34,頁807中)這段註解很清楚地指出法師的定義: 一、「法」:可讓人奉行實踐的軌則、法度; 二、「師」:言行舉止足以作為他人學習的楷模者; 三、「法師」:以「法」為學習標的的軌則、正法,而作為他人學習倣效的對象。 又《法華文句》:「法者,軌則也;師者,訓匠也,法雖可軌,體不自弘,通之在人。五種通經皆得稱師,舉法成其自行,皆以妙法為師,師於妙法自行成就,故言法師。」(大正34,頁108中)佛法能夠流通,還是要依靠人為的力量,若能以妙法為學習對象,於這些法義有所成就,佛法自然能夠弘傳無礙,而這弘法之人即是「法師」。 原始佛教時期,因說法重點的差異,對「法師」的詮釋,偏重於自我身心的觀察。《雜阿含‧二六經》:「若於色,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是名法師;若於受、想、行、識,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是名法師。」(大正2,頁5下)《雜阿含‧二八八經》:「說老、死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說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法師,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法師。」(大正2,頁81中)對蘊、處、界的觀察,或是透過十二支緣起彼此相待、互為因果,而認清諸行無常的事實真相,進而破除對自我的執著或產生的妄執邪見。原始佛教時期佛陀主要的教說,一切的修行方法皆是回歸行者身心,不只理論上的認識,更要自身確實地了解、體會。透過經文很明顯地看到,當時所謂的法師重於實踐,徹底從自我身心下手,如實地看到自己如何貪染五蘊,看到生命瀑流的生生不息,進而感受到執著所產生的苦迫而生厭,急於遠離以到達寂滅安穩之處。 深入的分析,《阿含經》中對五蘊、十二因緣的生厭、離欲,即是《法華經玄贊》中所指的「可軌可持」之法,《雜阿含》是將修行的方法與技術清楚地開顯,二者所指其實是一致的,只是詮釋上的開合不同罷了。不論是以「法」為學習標的的軌則、正法,而作為他人學習倣效的對象,或是能以妙法為學習對象的人,其最基本都是指能以法為師的人。因為能學習正法的人,才有教導他人學習的能力,足以作為他人的榜樣。 法師的資格
〔依身分〕
能以正法為師就是「法師」,然而法師一定是出家人嗎?《雜阿含‧二六經》及《雜阿含‧二八八經》中都沒有特別限定是出家僧人,但在《雜阿含‧二九經》:「若比丘於色,說厭、離欲、滅盡,是名說法師;如是於受、想、行、識,於識說厭、離欲、滅盡,是名說法師。」(大正2,頁6上)以及《雜阿含‧三六三經》:「若有比丘說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說法比丘;如是說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是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說法比丘。」(大正2,頁100下)則可知〈二六經〉與〈二九經〉內容一樣,只是〈二九經〉多了「若比丘」;〈二八八經〉與〈三六三經〉情形也一樣,〈三六三經〉較〈二八八經〉多了「若比丘」,茲將《雜阿含》四經表列如下:
《雜阿含‧二六經》 若於色,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是名法師;若於受、想、行、識,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是名法師。 《雜阿含‧二九經》 《相應部》〈因緣相應〉 一一五、一一六經 若比丘於色,說厭、離欲、滅盡,是名說法師;如是於受、想、行、識,於識說厭、離欲、滅盡,是名說法師。 《雜阿含‧二八八經》 說老、死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說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法師,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法師。 《雜阿含‧三六三經》 《相應部》〈蘊相應〉一六經 若有比丘說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說法比丘;如是說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是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說法比丘。 從上表可看出經文透顯出一個訊息:「法師」可能不一定是出家人!《雜阿含‧二六經》及《雜阿含‧二八八經》都只是定義「法師」,沒有特別指明身份,但在《雜阿含‧二九經》及《雜阿含‧三六三經》多了「若比丘」,解為:「若比丘對五蘊、十二因緣能夠生厭、離欲、滅盡,就是法師。」所謂「術業有專攻」,在法義及實踐上有所心得,自然能與他人分享。而佛法中所說的「法」,本來就是指世間一切真如之法,若能體解這些法爾如是之理,並躬身踐行,即使是白衣居士,當然也可稱為「法師」!但在北本《大般涅槃經》則說,佛陀能知法、知義、知時、知足等,所以稱為「大法師」(註一)。佛陀是三覺圓滿的至尊,其弟子也是煩惱漏盡的解脫聖者,皆知深妙之法,又能應眾生根機之利鈍為之演說,所以稱為「大法師」。但在南傳尼柯耶,只見能了知五蘊、十二因緣的內涵,厭離貪,朝向寂滅而努力,就是「說法比丘」的經文。如南傳《相應部》〈蘊相應〉一六經:「若比丘為厭離老、死,為離貪,為滅而說法者,彼得謂是說法比丘。」(註二)以及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一一五經:「若比丘為色之厭患、離欲、滅盡而說法者,應名為說法比丘。」(註三) 依《雜阿含經》及《大般涅槃經》二者得知,佛教的「法師」包括佛、菩薩、聖弟子、居士,只要能確實了知「法」,如法修持,則無論在家、出家身分皆可稱為「法師」,可說是「廣義的法師」。
〔依修學的內容〕 若依修學的內容來看,根據《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一及《十住毘婆沙論》卷七等所載,法師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法師十德 (1)善知法義,謂菩薩以無礙之智,善知一切諸法要義; (2)能廣宣說,謂菩薩以智慧辯才,廣為眾生宣揚如來妙法; (3)處眾無畏,謂菩薩處於大眾中善說法要,且隨其問難,皆能酬答,無所畏懼; (4)無斷辯才,謂菩薩之辯才無礙,所說之一切法,經無量劫仍相續不斷; (5)巧方便說,謂菩薩善巧方便,隨順各類機宜而說一切法,令人皆得通解; (6)法隨法行,謂菩薩說法令一切眾生如法而行,隨順無違而修諸勝行; (7)威儀具足,謂菩薩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無有缺犯,令人敬仰; (8)勇猛精進,謂菩薩發勇猛心,精進修習一切善法,化導眾生而無有退轉; (9)身心無倦,謂菩薩整肅身心,修諸勝行,常起慈心攝化眾生而無有懈倦; (10)成就忍力,謂菩薩因修習一切忍辱行,而成就無生法忍之力。 修行一切功德行願而作大法師,善能守護如來法藏,以無量之善巧智慧辯才,為大眾演說妙法,令眾生得大安樂,能具足這十項德能者,才有資格稱為「法師」。
◎行四法 (1)博多學,能持一切言詞章句; (2)善知世間、出世間諸法生滅之相; (3)得禪定智慧,於諸種經法中,能隨順而無諍; (4)不增不減如法而行,言行一致。 所謂「沒有天生的釋迦」,當然也沒有天生的法師。堪作為一位法師是需具備某些特別的條件,但這些條件除了先天的特質外,更需要後天的努力。能利用本身有的優越特質,再透過堅定的精勤努力,自然成就「法師」。要具有十德及行四法,須透過日常生活的修持,在聞、思、修中逐漸長養戒、定、慧,成就人天師範的道業。 法師的種類
以佛教而言,「法師」是一般的通稱,包括精通經、律、論的「三藏法師」,有偏重修禪的「禪師」,持律、研律的「律師」,以及闡釋經典的「論師」。事實上,出家人都可稱為「法師」,只是每人根器、用功法門不同,所以發展的方向也不同。如道安、慧遠等學問德行高深者,被稱為「法師」;鳩摩羅什、玄奘等對翻譯經藏有卓然貢獻,則被稱為「譯經師」;近代律宗大師「弘一法師」被稱為「弘一律師」等。 根據大乘初期的經典──《法華經》中的〈法師品〉及〈法師功德品〉,依法師之專長及其弘法之差異可分為受持、讀經、誦經、解說、書寫等五種,稱為「五種法師」,《辯中邊論》則演成書寫、供養、施他、聽、披讀、受持、正開演、說、誦、思修等「十種法師」。另外屬般若系論典的《大智度論》卷五十六則有「六種法師」,即: (1)信力故受,信指信向,受為領納之義。謂以信向之力聽聞正法,乃至一句一偈領納在心。 (2)念力故持,謂所聞之法,由憶念之力執持不失。 (3)看文為讀,謂目視經文,而以口宣讀。 (4)不忘為誦,謂習讀既熟,不假看文,自然成誦,無有忘失。 (5)宣傳為說,謂將自己所得之法,輾轉為他人宣說。 (6)難曉須釋,謂佛所說經教,義趣深遠,難以明曉,須經解釋,方能解悟。 《仁王經》中則有十三種法師,經云:「有十三種法師,謂十二住及佛是也。又於十方界佛滅度後守護受持如來正法,廣宣流布開化不絕為法師也。如辯積法師及那羅延法師他摩室利法師等,並由其人使佛法再興久住世間等,此為持正法法師也。覺諸魔事者,如莊嚴論中有魔詐現神通作羅漢形,惑亂諸比丘愚皆歸伏,有多聞比丘以阿毘達摩石磨之,假金遂露。」(大正35,頁275中) 依照以上幾種法師的分類,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不論何種法師,並不一定要為他人說法才能稱為法師。若能依自己的根器、興趣、信仰,對於法能恆常、耐心地修持,也能以此利益他人,就是一位如法的「法師」了。 法師應有的態度及作為
《妙法蓮華經》:「是諸王子,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悉捨王位亦隨出家,發大乘意、常修梵行,皆為法師。」(大正9,頁4上)大乘思想從佛本生中自利利他的菩薩大行發展而來,有別於《阿含經》中所提的法師──偏重於徹底了解自我身心的狀況,進而了解其無常生滅變化,遠離執著貪染達到解脫──反倒是著重在策勵菩提大願的開顯。《妙法蓮華經》中清楚地揭示:身為法師,要能捨棄世間最尊貴的物質享受及名聲,要能發起大乘利人之心,修持清淨行,這樣才足以堪任「法師」之名。又《大智度論》卷五:「大慈愍為眾說法,不為衣食、名聲、勢力。」(大正25,頁98下)大乘思想強調發菩提心,所有作為皆以能利益眾生為前提。不顧自身聲名、權利,而以法義與他人分享,這才是真正的說法。 既為法師,更要注意自己的身口意三業,所說所行必要以法為依據,不可錯解;若自己沒有聽過或不了解的地方,也不可隨意編造,誤人見解,出之無憑。所以《佛開解梵志阿魃經》中說:「沙門所說,言必法師,其所不聞,不得意造。」(大正1,頁261上)因為法的分享本是出於一番善意,源自於菩提大願,因此不可在自己尚不清楚時,加以臆測,否則原先的善意反而造成他人的傷害。又,在敷演教法的過程中,說者並非照本宣科,而是以醫者的態度面對芸芸眾生的各種問答,提供各類的答案,真能顯發諸佛如來法爾如是的真理,剷除種種的邪執妄見,令法音宣流無礙,才堪為說法之人。就像回答問題,答案必須能契合題意、言之有物。《法華玄論》云:「所言法師具問答者,弘道之人必敷經說論。經論之中有問答,巧申菩薩之難為能問,妙顯如來之通為能答;巧申外人之難為能問,妙顯論主之通為能答;摧破九十六種外道為能問,妙顯諸佛如來正法為能答;又能破三乘異執為能問,巧顯一乘同歸為能答。能問能答佛教宣流,故名大法師也。」(大正34,頁361上)所指的就是這破執顯正的工夫,而這也可說是具足如來智慧。 《大方廣佛華嚴經》:「佛子如是行,具足如來智,悉能分別說,諸佛甚深藏,若能如是說,法師中第一。」(大正9,頁462下)佛世時,佛陀及他那些優秀的弟子們,在當時存在諸多教說的印度,能以符合時下人心、圓滿無礙的教法,讓人們皈投信服,顯示出佛法是理契緣起的真如之法,而非虛無空洞。因此可以在眾說紛紜的教派中異軍突起,更顛覆原來婆羅門教派「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門至上」傳統、卻不公平的種種制度,引導人們追求身心的徹底解脫。所以《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三:「如《花嚴》云:作大法師具法師行,善能守護如來法藏,以善巧智起四無礙,用菩薩言詞而演說也。」(大正33,頁509上)只要具足「如來智」,且能了解、開演諸佛甚深秘藏,則是法師中的法師。
總結諸經論,可看出「發菩提心,慈悲度眾」,以及「具足如來智,勤修梵行」是身為法師所應有的態度。在修行路上,也應不斷地以此自我提醒,積聚修道資糧。
與法相應──現代法師的省思
出家是一條殊勝,但卻佈滿挑戰的艱難道路,即使供養不虞匱乏,但何德何能接受信施的護持?佛世時,佛子善根深厚,佛陀一聲「善來比丘」,弟子鬚髮立即自然掉落,顯現出莊嚴的沙門相。這些佛教沙門,遠離憒鬧,水邊林下精勤修行,每日一次回到人群中乞食以維持生命,物質所需雖然乏少,但在修練中逐漸地去除身心種種障礙,掃蕩各類煩惱習氣,終於轉凡成聖獲得解脫。然而現代社會進步的脚步太快,人的思想、思考不得不隨著改變,身為現代的出家人,在適應大環境的變遷之際,有時不得不作某些調整,即所謂的「隨方毘尼」。這樣的改變是必須的,然而思想可以很活潑,但卻不能違背佛法的真義。有些人在改變的過程中,模糊了佛法的原意,對修行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沒有沈澱下來思考所作所為,無法與法義、自我心靈對話,只是順著那股洶湧的潮流,不斷向前向前,最後可能會偏離原來的目標,背棄了初心! 回顧佛教的發展,歷代的祖師大德,從身口意所流出的作為總是那麼高超,深入經藏、統理大眾,一切以法為依歸,修行、作務,無一不是戰戰兢兢、夙夜匪懈地與初心相應,與佛陀一個鼻孔出氣!經典上說要踐行「法」、以法為師,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落實,便成了重要的課題。以一個現代的佛教僧人而言,應時時思考身為法師應有的作為,回顧世、出世間不共之處,不論根器、興趣如何,對法的勝解、繫念、奉行,應是歷千古而不變的。 不論時空如何變遷,「法師」就是以法為師的人,是教導他人修學「法」的老師。因此,身為現代的佛教法師,務必要熟悉經藏,並確實依法修練,以適應現代環境需求的方式弘法利生,時時以法為師、以法為軌,以法莊嚴修道生命! 註釋:
註一:《大般涅槃經》,大正12,頁468上。 註二:元亨寺《南傳大藏經》,第14冊,頁20,民國82年8月。 註三:元亨寺《南傳大藏經》,第15冊,頁231,民國82年10月。 http://hkbi.gaya.org.tw/journal/no8/classical.htm
|
| Home » » 認識真正善知識-蕭平實老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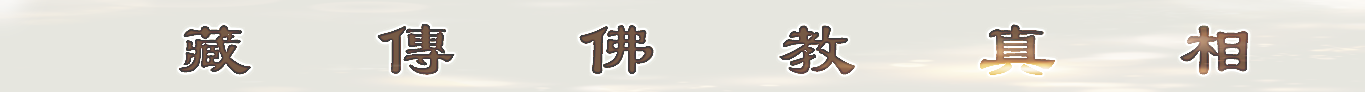
简体 | 正體 | EN | GE | FR | SP | BG | RUS | JP | VN 西藏密宗真相 首頁 | 訪客留言 | 用戶登錄 | 用户登出
- 評論南傳佛教上座部及印順法師
- 喇嘛教本質的海濤法師放生爭議
- 雙身法黃教祖師--宗喀巴(廣論)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淨空法師揭發邪惡之偽藏傳佛教開示輯
- 慧律法師破斥藏傳假佛教及「人間佛教」之邪說
- 淫人妻女之活佛喇嘛(偽藏傳佛教)性侵害事件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六字大明咒秘密大公開
- 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性醜聞
- 高僧學者名人批判雙身法之西藏密宗(偽藏傳佛教)證據大公開
- 藏密本質的聖輪法師性醜聞事件簿
- 雙身法達賴喇嘛秘密大公開
- 殘暴的偽藏傳佛教、西藏密宗、喇嘛教殺人證據
- 宗教性侵防治文宣教育(歡迎流通)
- 雙身法喇嘛教(西藏密宗、偽藏傳佛教)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紅教祖師--蓮花生(大圓滿)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雙身法白教祖師--密勒日巴(大手印)淫人妻女秘密大公開
- 真心新聞網、各家宗教新聞
- 漫畫-密宗活佛、喇嘛、仁波切
- 喇嘛教雙身法連載專欄:台灣玉教室
- 偽藏傳佛教雙身法分享專欄:-讀者來鴻
- 罪惡達賴 罪惡時輪
- 偽藏傳佛教(藏密)問答錄●學密基本常識
- Swami瑜伽性侵大師
- 人面獸心-索達吉堪布雙修大揭密
- 國學大師-南懷瑾雙修大揭密
- 卡盧仁波切雙修大揭密
- 索甲仁波切雙修大揭密
- 真佛宗盧勝彥雙修大揭密
- 破斥藏密多識喇嘛《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 陳健民上師講述如何修學密宗邪淫男女雙修灌頂
- 剖析天鑒網悲智版主愚癡言論輯
- 嗜血啖肉的人間羅剎---喇嘛教絕非佛教
- 嗜食糞尿精血等穢物的藏傳佛教
- 附佛外道-法輪功的秘密
- 揭發「藏傳佛教」轉世活佛的騙人內幕
- 認識真正善知識-蕭平實老師
- 偽藏傳佛教詩詞賞析
- 第一部揭開西藏神秘面紗的大戲--西藏秘密
- 破斥遼寧海城大悲寺妙祥法師抵制正法
- 破斥一貫道
- 破斥瑯琊閣
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當地已有民間信仰的“苯教”流傳,作法事供養鬼神、祈求降福之類,是西藏本有的民間信仰。
到了唐代藏王松贊干布引進所謂的“佛教”,也就是天竺密教時期的坦特羅佛教──左道密宗──成為西藏正式的國教;為了適應民情,把原有的“苯教”民間鬼神信仰融入藏傳“佛教”中,從此變質的藏傳“佛教”益發邪謬而不單只有左道密宗的雙身法,也就是男女雙修。由後來的阿底峽傳入西藏的“佛教”,雖未公然弘傳雙身法,但也一樣有暗中弘傳。
但是前弘期的蓮花生已正式把印度教性力派的“双身修法”帶進西藏,融入密教中公然弘傳,因此所謂的“藏傳佛教”已完全脱離佛教的法義,甚至最基本的佛教表相也都背離了,所以“藏傳佛教”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喇嘛教”也就是──左道密宗融合了西藏民間信仰──已經不算是佛教了。

